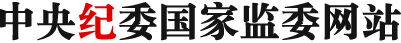编写完《美国宪政历程》,看着这些不知修改过多少遍的文稿,我如释重负,同时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除了撰写了几篇学术评论和时事评论外,我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本书的写作和编辑中。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受过专门系统法律训练的人来说,这个领域既充满了诱惑,也有很大的风险。不过,我想到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法学家兼法官(联邦第七上诉法院)波斯纳的一句名言:“法学应当使外行人也感兴趣,自己多少有点安慰。”如果法学能够使外行人感兴趣的话,也就无法排除感兴趣的外行人来从事有关法律的业余研究工作。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没有任何法律专业背景训练的职业法官和律师,而且,也没有法学教授来潜心写作美国宪政史的入门书,那么,由几位研究美国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来写作美国的宪政历程,作为抛砖引玉之用,看来也不能说太出格。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宪政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并不是法律专家的“非我莫入”的禁区。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法学院三年制的法学博士(J.D.)教育主要是一种法律职业训练,侧重于实用而非学术,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而法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则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综合,比如,经济系在政府经济法规、产权制度、反托拉斯法、公司法等课题,政治系在美国宪法、司法制度、立法过程、政治法律思想等课题,社会学系在法律社会学、犯罪学、刑罚理论等课题,历史系在宪政历史、宪法史、法律思想史等课题,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由于英美普通法传统和案例教学法的影响,美国大学的法律教育不可避免地与法律史和政治法律思想史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没有发达的法学教育,却有着庞大的法学学位获得者。我本人就是一个“法学”硕士。不过,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个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和绝大多数中国法学学位一样,并没有真正的“含法量”,因为我的专业学科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而中国的学位分类中,包括党史和政治思想教育在内的所有政治学都属于法学范畴。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培养的“法学”学位获得者之多,大概连“诉讼之国”的美国都望尘莫及。
1988年,在师从杨生茂教授六年后,我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了美国外交史方向的史学博士(博士论文后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随后南下金陵古城,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始了我的职业学术生涯,一直为中心的美国学生讲授中美关系和国际冷战史,间或也给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20世纪美国、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为促进中美两大民族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授课之余,利用中美中心丰富、精当和更新迅速的外文书刊,围绕着中美关系、中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一些学术研究和写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虽然成就不大,但自认为还算扎扎实实,研究工作开始有了驾轻就熟之感,一些研究成果也被同行学者所接受,用一句比较土的话来说,至少“混了个脸儿熟”。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对美国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9年夏初,南开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王正毅教授邀请我给“全球化和区域主义”国际讲习班学员作一个有关国际体制作用的主题发言。为此,我特地撰写《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一文(后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在南开期间,我与正在南开历史所义务讲学的美国宾西法尼亚印第安纳(Pennsylvania Indiana)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希博士邂逅。承他不弃,送我一本他刚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回到南京后,我很快就读完这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对美国宪政的丰富内涵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是年夏天,我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了“美国的世界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为题的中美年轻学者对话会。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金灿荣博士也是与会代表。他是我的老朋友,当年我们同在美国所读研究生,我比他高两级,我学美国外交,他读美国政治,但后来他师从北京大学袁明教授攻博,转向了美国外交的研究。会余时间,我们漫步在电影“sleepless in Seattle”(《西雅图夜未眠》/《西雅图不眠夜》)中出现过的海滨码头,一起交流读王希书的体会,得出了同样的看法: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且,美国人的宪政观和法治观对其外交的内在目标和外在行为方式都生产了重点影响。从美国人早期追求航海自由权、到威尔逊对国际联盟的痴迷、到罗斯福的“四警察”观念(即二战后由美英中苏四大国像警察一样维持各自所在地区的国际安全和稳定)和联合国构想,再到当前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不遗余力的倡导和推动,无一不与其国内宪政观念和法治经验密切相关。显然,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
这一考虑激活了我内心中对美国宪政法治的潜在兴趣。我过去对美国宪政一直有所注意,80年代初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给导师杨生茂教授写的第一篇读书报告就是《美国宪政史上的联邦法令废止权》(14年后,该文经大量修改后终于发表在《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1995年秋,根据自己在美国华盛顿的直接观感,为《读书》写了《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最近,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来信,告之他们将把该文编入日本的中文教材),随后,在研究美国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等弱势社会群体照顾性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时,更是涉及到不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民权案子。
2000年新学年开始,我毅然放弃了在前述“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一文基础后写作介绍美国“multilateralism”(多边体制论,也译多边主义)的计划,开始了自己在美国宪政史的探索和冒险。遗憾的是,比较美国汗牛充栋的宪政文献,有价值的中文著述实在是少的可怜。除王希书外,余下的似乎只有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与王希书按历史进程来讨论美国宪政的“史论”不同,该书按美国宪政的主要问题,对美国宪法原则进行了法理的分析。另外,台湾学者朱瑞祥写过一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史程》,以一系列案例穿起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演变。
还有两本翻译著作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是柯特勒的《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和Peter Irons的《为权益而战》。它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美国法治史上的冤假错案,和小人物为维护自己宪法权利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两本书,内容生动,评论犀利,非常精彩,在美国好评如云,的确反映出美国学者对本国宪政制度的批判精神和政府滥用司法权力的警觉态度。但是,当它们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就会出现误读的可能性,因为美国的一般读者对自己生活的法治环境有相当多的切身体验,也比较容易理解美国法治的“阴暗面”只是其完备法治的一小部分,但对于没有过在美国生活体验的一般中国读者,这一“阴暗面”可能会被不自觉地放大成为美国宪政和法治的全部,而且,由于作者是美国知名学者,作品又是有影响的著作,因而就增加了这种印象的权威性。中国的批判家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有必要强调美国宪政和法治的长处吗?美国人自己都说自己的法治问题成堆!”
这里的确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学者在挑选译介西方著作时,在突出我们的个人偏好时,一定要照顾到全面;在赞赏另类时,更应该突出主流。在人文学术中,有时新不一定比旧好,有时新可能还不如旧。在其名著“Politics among Nations”(《国际政治》)中,国际政治学权威Hans J.Morgenthau开篇就指出:“在政治理论中,新鲜突兀未必是优点,源远流长也未必是缺点。”不幸的是,中国学界似乎已形成了某种传统,译介近现代西方学术时较多地选择经典和主流,但译介当代作品时似乎更多地注意标新立异的枝干,而非源远流长的传统。在我看来,不同社会间的交往和交流应该跟人与人交往一样,尽量了解、借鉴甚至是学习对方的长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过多纠缠于历史的纠葛和偶然的冲突,陷于某种受害者、胜利者或救世主的心态而不能自拔,绝非是一个伟大民族自谦、自信和自强的表现。这绝非无的放矢,看看在过去的几年里中美两国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学者对相互嘲弄、彼此揭短甚至是攻击谩骂的热衷,就可见一斑。
这一观察确定了我从事美国宪政史探讨的一个原则: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后来者,我要虚心地学习和阅读其他学者的著述;作为身处一个法制远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会中的观察家,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制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在具体做法上,利用自己作为历史学者善于叙事、对细节的敏感和对美国历史发展背景熟悉的优势来讲述美国宪政法治发展演变的故事。于是,我打算以“美国伟大的(国会)法律和(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为题分别讲述十大判决和十大法律的故事。
当我向远在美国的王希教授和我的老朋友陈伟提出这一设想时,得到了他们热情的赞扬,并建议我把判决和法律分开来作。由于判决的案例故事如此丰富多彩、惊心动魄,它自然成为了我的首选。更为重要的是,老友陈伟与我不约而同地对判决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在我之前开始在国内的《读书》、《南风窗》和海外的《世界周刊》以及网上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和《国风》发表他的美国法律纵横谈。他的欣然加盟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和思想性,缩短了与读者见面的时间。
本书的合作成为我们近20年友谊的小小高潮。我们是东北师范大学(长春)1978级校友,我在历史系,他在政治系。1982年初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他报考了苏联东欧研究所,由此我们开始相识。我于当年如愿以偿,他却在赴京复试后马失前蹄,但我们一直保持了书信联系。198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苏东所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此后,我们有一段很愉快的交往,包括一起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供一份美苏关系的咨询报告,一起去采访原国民政府驻印度远征军副总司令郑洞国将军,探讨美援对中美抗日同盟以及中共、国民党、美国、苏联四角战略关系的影响。1990年前后,我们突然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产生了共同兴趣,从各种零星的材料中吃力地试图弄清楚周恩来1950年10月8日赴苏联与斯大林讨论苏联空军援助和中国参战的行程,弄清楚周恩来此行究竟是带着参战的决定还是没有?为此,陈伟采访了周恩来此行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经师哲引荐,他还采访了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但由于缺少完整的第一手档案资料,除了弄清楚周恩来的行程外,第二个问题还是一锅粥。所以,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研究除了留下一批认真讨论的信件外,并没有成果发表。这一困扰冷战史学者的“世界性难题”,直到1996年俄罗斯方面档案公开才最终水落石出。
陈兄后来留学美国,就读华盛顿大学并获得电脑信息技术硕士学位,成为一位数据库高级技术主管。1992年和1994年我两次赴美进修研究,都在华盛顿见到他。但1998-2000年间,我们的联系一度中断。1999年秋-2000年春,我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了一个学期的高级访问学者,太太和女儿同行,住在华盛顿远郊。2000年秋,我们恢复联系后,这才发现我们当时近在咫尺,住在同一个社区,我女儿琬洁和他女儿陈晨还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晨竟然曾无意中为琬洁当过英语翻译。那时,可怜的琬洁一句英文不懂,作数学作业时像国内一样把答案直接写在书上,老师比划半天她也不明白。老师只好请来高年级的陈晨,用中文向琬洁解释说,不要把答案直接作在书上,因为美国的教科书为学校所有,要传给下届学生。这虽然是戏剧性的巧合,但我宁愿把它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要我们的友谊延续到两个孩子身上。
陈兄不仅及时完成了他所承担的案例(就这一点,我就要深深地感谢他,因为他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完成这些写作的),而且审读了全部文稿,提出了极为宝贵的修订意见,同时他还对大到全书的整体构思、案例的选择,小到书名的确定、脚注的核对都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比如,他对我最初提出的“伟大判决”很不以为然,因为Scott案可以说是最高法院“最糟糕”的判决之一。这提醒我在案例的选择上不能仅仅着眼于“伟大”,而且要注意到“恶劣”。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决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也像凡人一样会犯错误,而且因为特定的地位会犯大错误。
为了书中某个术语的翻译、某个概念的表述、某个段落的安排、某个引文的核对,陈兄在过去一年中给我打来了十几个周末越洋电话,我们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直到电话卡用完为止。更不要说相互间的上百份电子邮件,无数次的稿件传送。由于文字处理系统的差异,我们在文稿修订方面费尽心机。他的认真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同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白雪峰博士也给我友好的帮助。2001年初夏,我参加了白雪峰的博士论文《沃伦法院研究》的答辩。这可能是国内第一篇以宪政史为题的美国史博士论文,写得相当扎实。白雪峰对沃伦法院处理的一些著名的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案件很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为本书贡献了三个精彩的案例故事。
这样一本小书还得到了两位资深美国宪政史学者的支持。2001年7月,我和国内15位学者一起参加了Hawaii大学东西方中心、北京大学主办的“讲述美国和中国”讨论班。讨论班上,我结识了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市立学院)社会科学教授、美国宪政史专家Laurene Wu McClain(伍淑明)女士,向她请教了有些不易在书本上获得的美国司法程序和地方法院的知识。作为华裔教授,我很希望她能够为我的项目撰写一篇有关华人的案件,2002年初她寄来《从受害者到胜利者》。接着,我希望她能再写一篇二战中日裔美国人受迫害的案子,她再次欣然同意,不过不是由她亲自来写,而是请她的丈夫、California大学伯克利校区法学院法治史教授Charles J.McClain教授来撰写。Charles教授还是该法学院法学和社会政策项目副主席(Vice Chairman,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Policy Program),研究少数族裔宪法权利的专家。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教授忙里偷闲阅读了部份书稿,并针对书稿的若干不足提了意见,写出一篇精彩序言。他在文中对美国宪法宗教背景和自然权利观念的精辟分析,对书名中“宪政”一词的题解,使全书大为增色。至于序言中那“不识抬举”的戏言,也体现出作者特有谦虚和幽默。
这一项目设计的初期,王希教授提出了非常专业的意见。美国South Illinois大学历史系教授、2000-2001年度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富布莱特学者Sam Pearson,对我所选择的案例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现任美国Truman总统图书馆馆长的Michael Devin博士。虽然他与这个项目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是,1998-1999年度他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教期间我们之间进行的无数次长谈交流,不仅让我分享了他对美国政治、外交、社会等各种问题的深刻见解,而且促使我重新认识象牙塔内学院派历史学家(academic historian)的社会责任。作为1999-2000年度美国公共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他给我讲述他是如何从一个只为同行而写作的学院派外交史学者,转变为一个以服务公众为己任公共历史学者(public historian)的个人经历。他讲故事的天才提醒我时刻不要忘记,只有生动的故事才会有鲜活的历史,才会吸引你的读者。
2002年4月,在书稿的第二稿完成后,我有机会陪同20多位美国国会两院议员在上海、南京和北京考察交流一个星期。这些议员有一半是律师出身,与他们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对美国的法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体验。曾经担任过Texas最高法院法官的众议员Lloyd Doggett,还和伍淑明教授一起为我写推荐信,帮我争取到Ford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小额资助,使我能够在2002年夏去Hawaii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客座研究四个星期,利用Hawaii大学的资料,借机对书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定稿。因此,我要感谢这些给予我帮助的机构和个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程亦赤先生曾经对这一选题很感兴趣,并从出版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遗憾的是,我根本无法在他所希望的时间表内完成编写工作。中国法制出版社社长祝立明先生对项目鼓励有加,促成本书的及时面世。对这两位编辑朋友,我非常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吴耘和女儿琬洁。我把应该陪伴她们的几个寒暑假和许多其他休息时间都用来写作和修改书稿。她们对我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理解,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吴耘还以她理解英文的卓越能力,帮助我弄清楚一些最高法院判决中复杂的句式及其含义。
在现代学术体制,这个既没有正式“立项”亦无任何机构直接“资助”的项目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敝帚自珍,想到它得到这么多海内外老友新朋的慷慨相助时,每每令我感动不已。朋友们的热情和友情,写作和编辑本身所具有的挑战性,以及这些故事所蕴藏的无限勇气、丰富哲理和超凡智慧,使这项工作成为我从未经历过的一次精神旅行,愉快无比,也使同期一些复杂繁琐的学术体制给我带来的种种不愉快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一小项目即将完成之际,国家教育部将我申报的“联邦最高法院与美国法治的历史实践”列为教育部资助项目。这样,这本书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现代学术体制的束缚,而成为资助项目的前期工作和阶段成果。
我真心希望,新的项目能够像这个“没有名分的项目”一样,带领我进行一次新的、更为愉快的精神旅行。(任东来)